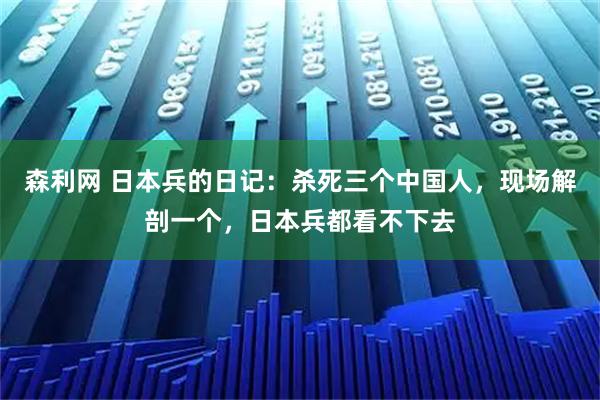
在侵华战争的血海里,有一段沉默太久的腥风血雨。不是我们忘了森利网,是他们太想让人忘了。
有人提起南京大屠杀,质疑证据;有人谈到活体解剖,说那只是“军事研究”。可偏偏,这些不是别人说的,是鬼子自己写下的,是刀口舔血的军医亲手记录的。
这篇“日记”,没有文艺腔,没有修辞,只有血——人血。
你要问“杀一个人得多狠”?我告诉你,这事连鬼子自己都看不下去。问题是,这不是特例,而是制度。这不是偶发,而是计划。
今天就打开这本血账,看看到底是谁,把“医学”变成了屠刀,把“实验”变成了人命。
“先杀,再剖,再扔坑里埋”——不是实验,是杀人剧本1940年9月上旬,南京的天气依旧酷热。热得是什么程度?热得穿军服的小林少尉看文件要眯眼,站在宪兵队门口的小笠原义利(时任军医、宪兵曾长)都懒得敬礼。
就在这段日记中,小笠原写道,他们接到了近藤新八大佐的命令,要对“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三个嫌疑犯”执行“秘密处理”。这个“秘密处理”可不是普通枪决,而是一场活人解剖的“现场教学”。
展开剩余83%被处死的,是三名中国工人,年龄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不等,被押到南京新发路宪兵队军官宿舍附近的“处理场”。两人直接被打晕扔进血坑,一人被指定为“医学用材”,做“战地解剖训练”。
解剖开始前,先是四个宪兵按住人,小笠原军医用针头注入毒素,观察中毒反应。随后,毒素未能立即致死,便改用手术刀切开胸部,沿乳头切至腹部,再剖腹“观察肝脏状态”。
现场用到的器械包括:柳叶手术刀、竹制倒钩剑、解剖剪、注射针筒、锯齿状开腔器械等。整个过程持续数十分钟,周围士兵表面麻木,实则眼神发虚森利网,有人直接退到墙角呕吐。
解剖结束后,尸体被扔进同一个血坑。桐原、山垣内、太田曹长三人负责掩埋。坑边血水已溢,尸体堆积如山。据小笠原日记记载:“这里每天杀几十人,每铲子下去都是人骨。”
“谁说是实验?人家分明在‘比谁更狠’”你以为那是解剖课?错了,那是“杀人比赛”。是日本宪兵在战场之外,比狠、比快、比谁能不眨眼地剖人心肝。
被选中“解剖”的那位青年,挣扎了一下,刚被毒针打进体内,表情痛苦得脸都扭曲。但毒素没起效,小美野伍长急了,开口就是:“用刀!从这开!”随即拿起大手术刀,从胸切到腹,一刀接一刀。
一旁的桐原和太田不光不劝,还起哄:“今天晚上终于可以下手了!”这种话,不是玩笑,是兴奋。因为他们早就安排好每个人轮流“动手”,哪怕只是把刀递给解剖者,也要来凑一脚“战绩”。
被挖出的肝脏被直接扔在地上,士兵用脚拨开,还顺口点评:“这是肿胀”、“这是萎缩”。而当切到肺部时,有人甚至说:“这块颜色不错,像条青筋。”
25秒,30秒……受害人在现场挣扎、口吐鲜血而亡。数名日本兵突然爆发生理反应,或后退,或作呕,其中一个直接高喊:“鬼子!日本鬼子!”
当时的太田曹长冷笑回应:“你怕啥?我们早就不是人了。”是啊,不是人了。不是人,才会踩碎脊骨当游戏,才会笑着切掉乳部,再问:“这块肉值几分?”
“不是突发,而是制度写进骨子里”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几个日本兵的“变态行为”,但从资料来看,它是一整套“军事医疗训练”的流程,是日本军国主义制度性暴行的冰山一角。
小笠原义利明确写道:这是在上级命令下实施的“医学解剖演练”,属于“宪兵队伍医学教育”的一部分。不仅有医护人员在场,还有宪兵指导、翻译记录、执行者轮流操作。
所有参与人员都有明确分工:有的解剖、有的打麻药、有的记录时间、有的专门负责踩断脊椎、掩埋尸体。
更重要的是,这不是一场,而是日复一日,批量进行。日记里写:“每天几十人,挖哪都是人骨。”这意味着,无数中国人被当成‘耗材’使用,为他们的“医学进步”流尽鲜血。
甚至到最后,当场有士兵对这血腥的景象表示不适,小笠原还振振有词地说:“我们是为了战争的胜利,为了和平的未来。”这就是他们的逻辑:为未来,可以今天杀人。为了“医学”,可以屠村毁城。
但真正让人心寒的是,他们不是在前线,而是在南京街头,在城市一隅。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,而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平民工人。有人还穿着工作服、有人连鞋都没脱,连喊救命都没来得及。
最后一个被解剖的青年,躯体还在抽搐时,小林少尉蹲下对他说:“少尉,可以干了吗?”然后挥刀——这一刻,被记录在案,也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。
参考资料:日本鬼子--军医的露天解剖(小美野义利) 三光————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.世界知识出社.1990森利网
发布于:河南省爱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